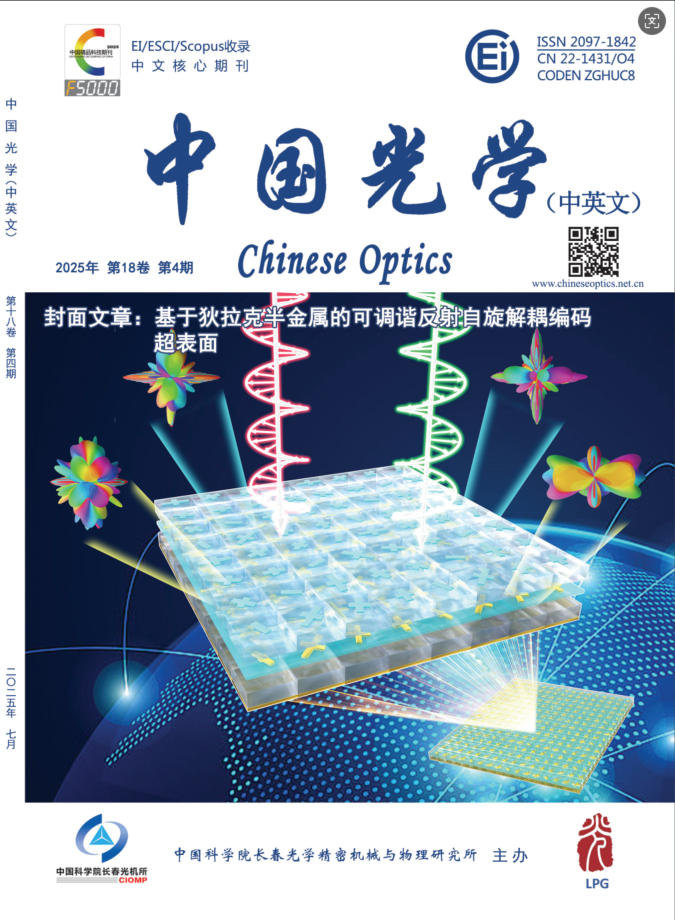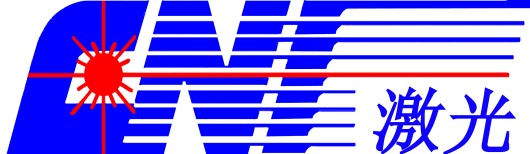人物小传

邹广田,1938 年 7 月 18 日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静态高压物理和超硬材料研究领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
1965 年研究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固体物理专业,现为吉林大学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长期从事静态高压物理和超硬材料研究,领导创建了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际上最早开展地球及行星内部物质的高压研究的物理学学者之一,也是国内超硬多功能薄膜材料和多功能高压相材料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为我国高压科学和超硬多功能新材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
艰难求学,难忘母恩
1938 年 7 月 18 日,我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我父亲毕业于吉林法政专科学校,在秦皇岛的司法科工作过。后来受到战乱的影响,我们全家逃难迁居到济南。1945 年 10 月的时候,父亲因为肺病去世了,母亲就带我和我弟弟回到了东北老家。
在东北老家呆了一年后,母亲带我们兄弟俩到了长春。我在长春读了一年小学三年级,因为解放战争的原因,母亲又带我们去边境呆了大半年。等到长春解放之后,我回来继续上学,可是就到了该上四年级的年纪了,这中间落下了一年的课程,升级考试的过程很是“惊险”。考试内容是小数点相加,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小数点代表什么意思,但我猜想应该把小数点对齐,剩下的地方相加,恰好猜对。于是得以顺利升学,继续念书。
那阵子我们经常帮老师写写“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之类的标语,偶尔也会上街去作宣传。当时的国际形势确实很紧张,犹记得我们会在东四小学里面挖防空壕。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我们会拿着小瓶子、夹子,戴手套、口罩去抓墙上那些没见过的虫子,假想那是别国发动的“阴谋”。可以说,爱国主义思想是在小学就开始培养了。
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去医院慰问伤病员,给那些伤病员献花、唱歌。因为年纪小,我们开始时不免有些畏缩,不过好在他们都非常和蔼,拉着我们的手说话,我们很快也就不那么害怕了。战士们脸上被汽油弹烧得都是疤痕,皮肤都烧没了,看上去很吓人。虽然还不太懂什么国仇家恨,但是我们看着他们脸上缠着的纱布,也萌生出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痛恨那些侵略者。
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才 28 岁。父亲临终前交代我母亲,只要能保护好我们兄弟两个,把我们俩送回老家就行,我母亲可以再去成家。但我母亲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独自抚养我和小我三岁的弟弟长大。
在搬到长春之后,母亲做过很多的杂活。当时出口大豆,大豆里面会有叶子、碎粒,她就干过一段挑豆的工作。后来,又母亲又经人介绍去粉笔厂做粉笔。厂子里要做彩粉笔,但是彩粉笔所需要的颜色大家都不会弄,就得学。我母亲没正式上过学,文化水平较低,学起这些东西来就很困难。而且粉笔厂离家很远,上下班的路程也只能靠腿走。当时厂子里开了培训班,但上课的时间不固定,有的时候在早上,有的时候在晚上,我母亲跟班就学,上完晚课回到家就已经半夜了,那时候我和弟弟都已经睡着了。我记得有次下雨,母亲下班回家的路上掉到胡同的一个大坑里面了,喊了半天才有人救她出来,真是又惊又险,可母亲却不以为意。因为母亲踏实肯干,后来被粉笔厂评为三等劳模,给了个本子做奖品,这个本子我直到今天还留着。
母亲的辛苦我们看在眼里,且那时候我们的学习还比较轻松,没那么多作业,所以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挣点小钱贴补家用。早晨我会去跑腿、送送烧饼什么的,一趟的报酬也就是一个烧饼。闲暇的时候我会买一些生玉米,煮熟后拿到街上去卖,虽然挣不了几个钱,但起码能解决自己的书本开销。到了暑假,很多同学会去参加夏令营,但是我从未参加过,因为我要趁天热的时候多卖几根冰棍。
到了中学时期,我一位堂兄每月给我们家寄五块钱。在他的帮助下,我家贫穷的状况终于得到了些许缓解。但是小时候养成的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却始终未曾改变。
二
结缘附中,得遇良师
那时的小学分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本来应该念完六年级再升中学的,但恰好那年是由春季开学改为秋季开学,所以我们少念了半年六年级。当年刚刚转学到长春的时候我的成绩一般,后来逐渐提高,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考了个第一名,也就拥有了保送“师大附中”(全称为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资格。在师大附中,我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学业,也收获了陪伴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师大附中一直强调的一点是“一定要掌握好最基础的东西”,有点像现在常说的“素质教育”。那时有句话叫“当你把念书时候学的那些东西忘得差不多以后,你最后记住的那些东西,是对你一生最有用的东西”,我到现在都深以为然。现在回想起来,中学时候学习的一些公式,后来如果不常用到,也就逐渐淡忘了。但老师们的一个手势、一个口头禅,却让我几十年后都记得很清楚,这种影响是深远的。
师大附中老师们的授课水平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大多是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尖子生,业务能力过硬。现在的老师可能会留很多作业让学生刷题,我们那时候不这样。老师会讲最基本的原理,然后出一些题让你自己去做。现在回想起来,附中的教育对我们的要求是要自己钻研,自己下功夫找书看。老师讲完之后留下的一些问题,你在自己思考过后,下次上课的时候拿出来问,这样才能进步得更快。
那时候因为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书可看,经常感觉题有点不够做,所以我们就搞了课外学习小组,大家一起研究感兴趣的方向。我当时参加了很多小组,像数学的、物理的,还参加了合唱小组。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小时候去慰问伤病员的时候就给他们唱歌,这爱好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减压方式。当时的音乐老师还建议我专职去唱歌,要不是实在舍不得物理,我也许就真的成了“歌唱家”。
学校会在周三和周六的下午,邀请学者来给我们作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带给我很大的启发,拓展了我的视野,像杨辉三角形、斐波那契数列,都是我在报告中学到的内容。当时书店正好有相关的书,我们就买回来自己看。我买过两本挺厚的日文旧书,一个是几何学,一个是代数学。我虽然看不懂日文,但看了书上的图和公式,也大概知道是给什么条件,求证什么东西。书的后面是一个相当于习题详解的内容,我们的学习小组就一起在这书上找题来做。
1954 年我考上师大附中的高中,还在班里做过两年班长。当时我们晚上可以在学校上自习,这种自习都是自愿的,想来就来,住在市内的可以早点回家,想我这些住在学校的就只要在宿舍熄灯前回去就行,但基本上全班的同学都在。有时候老师吃完晚饭就过来了,听同学们讨论讨论,遇到共同的问题。老师也会走到讲台上给大家讲讲,纠正一些错误。
我高三时的班主任是教化学的赵老师。有一次,赵老师上完课之后,有同学问问题,赵老师对我们说她家有事,得尽快回去。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作为班长,就跟着老师出去追问老师家里出了什么事,需不需要我们帮忙,赵老师这才跟我说她的孩子发烧了。正好当时是午休,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帮老师把孩子送到了医院。老师们真正地把我们这些学生的课程当成比她自己的孩子还重要的一件事,这让我们非常感动,也更加刻苦学习。
还记得有个滑冰滑得非常好的历史老师,有天下午上课,铃响了几分钟后老师才急急忙忙地跑来,说对不起大家,他的手表停了,耽误大家几分钟,然后开始给我们上课。那堂课老师没有带书本,但课还是讲得十分精彩。下课后,老师说这不是小事,他得赶快去检讨,然后竟真的自己跑到教务处检讨去了。老师们的这种敬业精神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等到我自己工作后,在对待同事、学生时,也始终秉持不分大事小事都要认真负责的态度,不敢怠慢。
我非常感谢我在附中的老师,他们对我产生了悠久的影响,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后来我评上院士之后,第一个去看的就是我的中学物理老师,那时老师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了,但一听说我来了,他还是非常高兴,看上去一点没有老年痴呆的样子,这可能就是老师看到自己学生成才的欣慰。我看着我自己的学生从一开始的啥也不懂,到出了问题马上就知道拆哪、修哪,也是一样的情感,这是师生之间的代代传承。
我的物理老师和化学老师是两口子,在这对夫妻的引导下,我对物理和化学这两门学科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当然都希望让我选择各自教学的专业,但是在我心中还是物理占了上风。
我对物理这门学科的喜爱是可以说是矢志不渝的。当年因为家里穷,我本来是打算初中毕业以后念中专,早点毕业出来工作给家里减轻负担,但是后来钻到物理里面,我就没舍得停下。母亲通情达理,也非常支持我们读书,说“你们愿意怎么念就怎么念,念到什么时候我都供着你们”。
后来,我考上了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的物理系,在物理这条路上坚持走了下去。可等到念研究生的时候,我又开始思想斗争了。那时候念研究生给我们的薪水是四十二块钱,而大学毕业出去工作的话是挣五十六块钱。十几块钱可能看上去不多,但我母亲那时候每个月就挣三十块钱,每个月多十几块钱就会让家里的生活状况好很多。
当时我有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是中学时的一班班长(我是二班班长),后来一起考到东北人大物理系的。他劝了我好多次不要放弃物理,我就在他的鼓励和陪伴下坚持读了下来。
学校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需要买一些物理相关的外文书,一本就要好几块钱。学校看我们没有钱买书,就给我们每学期报销二十块钱的图书费。
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每个月就能挣六十二块钱了,弟弟也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情况彻底缓解了过来。
现在回想起来,这条物理之路坚持下来实为不易。后来我在遇到需要“坐冷板凳”的时候,往往更能“坐得住”,这也是一路走来养成的信念。
三
两位前辈的教诲
我现在在做高压领域的研究,但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在 1962 年我本科毕业之后,是跟着苟清泉先生读研究生,学习固体理论领域的相关知识。
在 1963 年召开的物理学年会上,钱学森先生作了报告,号召大家做一些与尖端的技术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比如高温气体、高压气体、高压固体方面。钱先生作完报告之后得知苟先生在做这方面的研 究,就和苟先生谈了很久,反复强调基础研究一定要知道应用背景,而我们现在急需的基础研究掌握不够,需要苟先生在这方面多多努力。会议结束后,苟先生就开始抓紧部署这几方面的研究。当时我负责进行高压固体方面的计算,最开始是用手摇计算机,后来是用 A103 计算机。
到了 1966 年 2 月,力学学会和物理学会联合召开了原子分子物理与物理力学学术研讨会,有很多人参加。钱先生和苟先生分别做了大会报告,然后是分组报告,我被分到了高压固体组。那天我是下午 报告,当我来到会场的时候,发现会场外面还停着一辆防弹吉普车,我意识到钱学森先生也在现场。于是,我在完成了“统一高压状态方程和能带在高压下的变化”的报告后,趁会议休息的间隙,拿着我的毕业论文来到钱先生身边说:“钱先生您好,我是还没入伍的‘新兵’,请您多指教。”钱先生一边认真翻看我的论文,一边开玩笑说:“还没入伍就写这么厚一本,这入伍还了得!”我赶紧说:“谢谢钱先生的夸奖,我做的还不够。”钱先生又告诫我:“高压是非常有用、非常有前途的一个领域,但我们对它知之甚少,长期坚持下去必有所获,必有所成!”这些话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每每想起,便备受鼓舞。
会议结束后,我立刻回到长春继续高压领域的理论研究。后来,苟先生提醒我不能只做理论,还得做实验。正好第一届高压会结束后有一本文集,我就买来了,研究实验仪器相关的内容。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摸索实验和理论相结合的路子,只是还没有具体实施。那时苟先生在研究金刚石,我就跟着他做了一些实验。记得当时有个项目是协助二十一所做延时状态方程,把很多石头车成小柱做实验,那个实验是我设计的,我还保留着当时的一些手稿。我们还举办了全国首届人造金刚石短训班,有十几个系统、二十几个单位、将近五十人参加,我在里面参与了三个月的授课。
钱学森先生强调基础研究要跟尖端技术相结合,要学会如何把微观的东西通过统计的办法变成宏观的技术。苟先生把这个思想扩展了一下,他把技术抽象出来变成理论,如果这个理论问题你解决了,对应的技术问题也就有迹可循,苟先生的很多研究中都能看到这种思想方法的影子,像那时候提出的触媒的机理、选择的机理,都是这种思想方法的产物。我在前辈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方法,这些宝贵的经验铺就了我在高压领域不断前进的道路。
后来在出国结束时,我毫不犹豫地谢绝了毛河光和彼得·贝尔两位国际著名科学家的挽留,回到母校吉林大学继续高压物理的研究。前辈们交代给我的任务,我绝不敢忘。
四
走到国际前沿去
1980 年开始,我在美国呆了两年半的时间。当时有人问我为什么到美国来,我说美国的技术先进,尤其是他们的实验条件能让我学到、做到很多东西。
那段时间真的是一刻也不敢浪费。每天早上我都是第一个到实验室的,晚上别人都走了,我就用小厨房的煤气灶做点饭吃继续干。住处大概离实验室三百米,里面只有床和一个烧水的水壶。周末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也不休息,抓紧一切时间,所以很快就做出了一些成果。那两年多我发了十几篇论文,参加了很多会议。我记得我是在到美国半年以后参加了第一次国际会议,也作了报告,让大家知道在高压这个领域中国人都在做些什么。
要想走出去,走到国际前沿,首先你得学会跟他们交流。我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很吃力,因为他们说的那些英语包括很多缩略词和代称,根本听不懂。比如他们说“巴谋”,我就很困惑,后来才知道是“巴尔的摩”的简称,把中间的音节省略了就叫“巴谋”。还有“卡泰克”,指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这些词如果不知道,交流起来就很费劲,好在后来也就慢慢掌握了。
我在留学的时候,大使馆召开过一场关于大家在国外如何才能学好的座谈会。当时有种看法是,我们在国外应该只听课,因为听课是学知识,是“收入”;如果我们去做实验、给老板干活,这就是没必要的“支出”了。我就不同意这个看法,我坚持认为在国外能不能学好的关键,是认清我们来这到底是要干什么。我的目的很明确——我出来,就是要通过在这里的学习把中国的高压领域研究做到国际前沿。
学习有很多种方式,看文献当然是其中一种,但是看文献这个事情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既然在中国也能看,何必还要专门跑到美国来看?还有人说,回去想开门课,所以就以听课为主,但是我觉得听课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学过这些课了。有些课程,比如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甚至是我们研究生一人研究一章小组自学的。
对我而言,我来到美国,是一定要参加到实际研究中去的。只有深入参与进去,才能学到真东西,学到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法。实验方法、实验技术,这些都是要在实践中去领会总结的。
关于要不要“干活”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有争论。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说现在的研究生只是给老板干活的“打工仔”。但如果这么说的话,“老板”也很辛苦。学生要发表文章,哪一个稿子也不是发过去就能马上接收的,都得翻来覆去不知道做多少次的修改。这个过程,其实还是老师和学生一起不断成长的过程,而不是单纯地“干活”。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非得发论文不可,这不成了“唯论文”了吗?我觉得,论文很重要的意义之一是把科学进度记录下来,让我们可以去跟外面进行交流。参加学术会议或访问实验室,彼此互相交流,这样才能做到国际前沿。如果固步自封,你就会落后于人。
五
学无止境
我在附中的时候,老师就教导我们学习是个长期的过程,绝不是今天学完了以后,明天就不用再学习了,这个话我一直牢记到现在。人在哪个阶段都得不断的学习,不是你大学学完、研究生读完就能告一段落的。
我们完成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新一代大型超高压产生装置”项目,历经八年的攻关和设计建造,完成了六万吨的压机项目,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评审验收。但这只是我们过去的成果,我们还得向前看,不断去挑战新的事物。
现在我们实验室有很多新的研究方向,包括新型的超硬材料、高压下的发光、高压下的超导……实验室算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需要做的东西还有太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高压下的超导,虽然实现了材料在高压下的超导电性,但一旦释放掉压力,这个性质就消失了,下一步我们就要想办法实现释放掉压力后让材料仍能保持高压下的特性。
现在不断有新的挑战来到我的面前,而且这些挑战在我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遇到挑战,潜心去做才是正道。对我而言,未来的工作还有很多,实验室建设、学生培养、开拓研究方向,这些都需要很多精力,都需要不断学习。我们实验室的仪器大部分都是自己搭的,我常教导学生,有什么需要就搭什么仪器,这样你就会对设备非常了解,出了问题就知道根源在哪,学、做不分家,才是进步之道。
现在我已八十多岁,也还是经常看文献。如果不看,就不知道别人都在做什么。不断地“补”文献,每个礼拜再和学生讨论讨论,这样才知道别人都在做什么、做到哪了。
“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早已被人说得烦了,但实在是越品越觉得有理。不学不行啊!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实自我、克服挑战,这样获得的满足感,也最能让我感觉到收获的喜悦。
六
搞研究,要“甘坐冷板凳”
在当时钱先生的呼吁下,国内有很多单位都开始做高压领域的相关研究。但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实验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一小对金刚石就得五千块钱,而压碎的情形却很常见。
还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有次半夜十一点多做实验压碎了一个金刚石。当时仪器里面充了氦气,正在研究铁在高压下的相变,加压的过程中金刚石就突然碎了。在金刚石上滴上油后还出现了冒泡的现象,大概是因为有很多氦气都进到晶格里去了。我利用实验室里的摄像装置把整个过程记录了下来反复观看,思考其中的原理,但破碎的金刚石当然不可能再恢复如初。
我非常紧张地给负责人打电话汇报,他却很平静地说:“可能碎了不止一个金刚石,配对的那个可能也压碎了。明天上班仔细检查一下,不要紧,我再给你一对。”我十分抱歉,他却说不用道歉,这在科学实验过程中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等回国后,因为资金和设备的短缺,实验是很难进行的。
那段时间实验条件十分艰苦,要设备没设备,要技术没技术,所有工作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真的是咬牙在坚持。
因为种种现实原因,有很多曾经从事过高压领域研究的人遇到了新的机遇,就转行去做别的了,甚至有很多学校的高压领域研究完全停止了。我们几乎是在孤军奋战,直到后来苟先生去了四川大学,川大那边也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
现在看来,我们坚持的结果是好的。我们建成了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最早实现百万大气压的实验室之一,完成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新一代大型超高压产生装置”项目,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评审验收。这个单缸液压机可以称得上是国际上最高吨位的,可以帮助开展以前所不能进行的高温高压研究工作,极大地推进高压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不仅实现了我国大腔体超高压装置从无到有的突破,而且在物理、化学、材料、地学和能源等基础学科的高压科学研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参与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将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高压研究平台,在将来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好的手段、没有好的设备,根本就没法做出好的工作。实验室的建立必须得自己亲手完成,不做不行。如果一遇到什么实验难题就求助于国外,那必会一直受制于人。比如一个这样的实验——把金刚石做到几百个微米的尺度,就能达到五六十万倍大气压,然后在上边放个铜丝或者金丝,测量样品电阻。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必须有自己的实验设备、实验方法,慢慢探索研究,才能一步步达到这个目标。后来,我们就在金刚石上生长我们想做的图形,这样做出来的精度很高。
做这些东西的过程中,自己发展的高压技术、设备,可以自己调试。只有自己清楚这里面的个中原理,才能进行针对性的改进。现在我们实验室里做高压拉曼光谱的设备就是我们自己搭的,实验精度完全不输于市场上能买到的设备。
从实验室的建设、实验方法的建设发展到大科学装置的建设,都需要长期的规划。如果只顾眼前的工作,那是万万不够的。但是这类长远计划的开头必然非常艰难,甚至根本申请不到相关的经费。
比如我们当时做金刚石膜时的经历:我去教育部答辩,有人说国外刚刚在显微镜下看到成像是个小方块,尚做不成膜,你就能做出来吗?即使能做出来,做不到想要的图形有什么用?然后这个项目就被否决了。
好在后来一汽集团的工艺处长问这个金刚石膜能不能用到车刀上,我说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可以在车刀上做成膜。他非常感兴趣,表示如果金刚石膜能做到车刀上,那是有大用处的,因为常用的车刀有点软,而单晶金刚石车刀成本又太高了。1985 年他们给我们实验室支持了几十万元的研究经费,给我们下了明确的任务需求,第二年我们就把产品做出来了。
后来我们参加“863”计划,一开始给我们的经费也是比较少的,但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的成果比其他人完成得好,经费自然而然地就增加了。
在这些年的坚持下,我们研制出了国内第一片金刚石薄膜、世界上第一片按设计图案选择性生长的金刚石薄膜、第一片异质外延单晶金刚石膜,在国际上首次将 CVD 金刚石膜用做半导体激光器的热沉——这个热沉刚刚做出来的时候没人用,因为太贵了,高昂的成本让这项技术显得鸡肋。但这项技术现在派上了大用场,因为它是解决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散热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
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下,整个高压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所以对科研人员来说,你必须长期坚持一个方向,这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要有“甘坐冷板凳”,无人支持也咬牙挺住的韧性。稳稳地坚持下去,再冷的板凳,也有被焐热的一天。